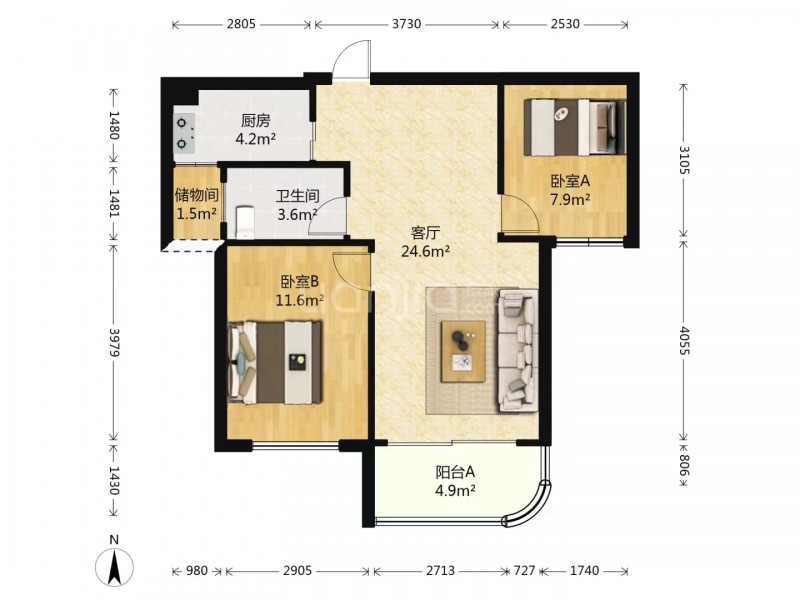漳州“抗战诗星”杨骚,打破“文人无用”偏见,以笔为刃斩向敌寇阴霾,用诗作鼓擂响民族复兴战歌——
诗剑破苍冥 战火铸魂骨

杨骚在抗日前线的小村庄休息
1900年的漳州古城,一户普通人家迎来了男婴杨古锡,谁也未承想,这个不到周岁便过继给堂叔杨鸿盘的孩子,日后会以“杨骚”为笔名,在文坛书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。杨骚(1900—1957),福建漳州人,著名诗人、作家,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,中国诗歌会发起人之一。“骚”字虽随意取之,却有其涵义,既是他对社会现实的隐晦批判,也预示着其一生特立独行的精神底色。
杨骚于1938年加入“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”,1939年参加“作家战地访问团”到抗日前线访问,被誉为“抗战诗星”。“皖南事变”后在新加坡主编闽侨总会的刊物《民潮》,开展抗日宣传。杨骚出版有抒情诗集《受难者的短曲》《春的感伤》等;剧本集《迷雏》《他的天使》;诗剧集《记忆之都》;评论、随笔集《急就篇》。译作有《铁流》《十月》等。
少年意气
烽火燃情启文章
杨骚5岁入私塾,14岁考入省立第八中学,自幼便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质。他痴迷小说与杂书,敢于在长辈议事时插话论理,遇有恃强欺弱之事必挺身而出,举止间透着名士派头。这种少年时期的品格,成为他日后投身革命文学的精神谱系。
1918年,怀揣求知与变革梦想的杨骚东渡日本留学。在日本,他首次接触到进步文学思潮,思想逐渐觉醒。1927年回国赴上海后,杨骚幸运地得到鲁迅的教诲与提携,成为《语丝》《奔流》等重要刊物的撰稿人。彼时的上海,风雨如磐,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兴起,社会底层的苦难与旧世界的丑恶,让杨骚毅然拿起笔作刀枪。1928年,他在《奔流》创刊号发表诗歌《把梦拂开》,“赤着膊/挺着胸/光着腿登上望台”的激昂诗句,将斗士姿态展现得淋漓尽致,也标志着他正式以文学为武器,向黑暗现实宣战。
1930年3月2日,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,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事件。杨骚不仅成为左联早期成员,更身兼创作委员会成员、小说散文组成员,同时担任诗歌组负责人之一。左联时期的杨骚,不仅在文学创作上发力,更直面白色恐怖的考验,冒着生命危险上街贴标语、发传单,化身地下工作者,用行动践行左翼文人的使命。九一八事变后,杨骚更是冲在抗日救亡前线,作为26名发起人之一参与成立上海文化界反帝同盟,发起中国著作者协会,为争取言论自由振臂高呼。这一时期,他创作的长诗《小兄弟的歌》充满革命激情,“摧毁腐朽旧世界”的呐喊,成为鼓舞民众的精神力量。
在诗坛流派纷争的年代,杨骚与同道诗人深感新月派、现代派诗歌脱离大众,遂于1933年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,担任四名常委之一,亲自创作实践“大众化、通俗化、革命化”的诗学主张,诗风从此实现重大转型。
即便1934年国民党政府查禁149种文艺书籍(包括杨骚翻译的《铁流》《十月》),也未能阻挡他的创作热情。他将目光投向家乡漳州,历时两年创作长篇叙事诗《乡曲》,于1936年发表在《文学界》创刊号。这部以漳州“乌石暴动”为背景的作品,分“写信”“黎明”“骚动”“锄声”“短简”五章,既描绘农民反抗压迫的“狂野风暴”,也饱含人性温情,被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评价为“展现农民‘打碎乌黑大地’的愿望与信心”,成为杨骚创作生涯的里程碑。
上海十年,是杨骚文学成就的爆发期。他先后出版随笔评论集《急就篇》、诗集《春的感伤》、诗剧集《记忆之都》,翻译《没钱的犹太人》等近20种著译。1936年5月,他创作的《福建三唱》以敏锐的洞察力预见战争阴影,字里行间满是家国忧思,被誉为“南方的《松花江上》”,成为抗战前夕极具影响力的爱国诗篇。
战火淬炼
诗文为刃御外敌
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,中华民族陷入危亡时刻,杨骚的人生轨迹再次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。他受郁达夫邀约南下福州,牵头组织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,担任抗敌后援会干事,主编《抗敌导报》,并在《小民报》发表《展开全面抗战》一文,疾呼“以牙还牙,为民族解放展开全面抗战”。在福州的日子里,他白天组织救亡宣传,夜晚伏案创作,用诗歌、杂文唤醒民众斗志,成为当地抗日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。
1938年底,武汉、广州相继沦陷,杨骚辗转抵达重庆,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(简称“文协”)。其中,杨骚发表的《莫说笔杆不如枪杆》堪称经典——“让我们的每只字,变成手榴弹!让我们的每个标点,是杀敌的子弹!”直白有力的诗句,打破“文人无用”的偏见,成为抗战文人的精神宣言。
1939年,杨骚主动请缨加入“作家战地访问团”,克服山路崎岖、物资匮乏的困难和严重的胃病,深入陕西、甘肃、山西太行山抗日前线采访。白天跟随部队行军,夜晚在煤油灯下记录见闻。这些战地诗歌,后来结集为《半年》出版,成为研究抗战时期敌后战场的珍贵文献。正如当时报纸评价:“作家战地访问团的意义,在于让文化人走进战场,用文字架起军民沟通的桥梁,粉碎敌人的文化阴谋。”而杨骚用行动证明,文人的笔杆,同样能成为抗日的“武器”。
1941年,皖南事变爆发后,国民党顽固派加紧迫害进步文化人士,居住在重庆曾家岩50号的周恩来,个别召见了杨骚。多年后,杨骚在自传中清晰记录下当时的场景:“周恩来同志指示我,‘到星洲(新加坡)后首先应帮助陈嘉庚先生’,团结华侨支援抗战。”这句嘱托,成为他此后在南洋工作的核心方向。
同年夏,杨骚经香港抵达新加坡,被陈嘉庚聘任为南洋闽侨总会刊物《民潮》的主编。亲力亲为,制定“宣传抗战、团结华侨、反映侨胞心声”的办刊宗旨,呼吁南洋文化界“用文字配合前线炮火”。在他的努力下,《民潮》从创刊时的30多页,半年内扩展到120多页,栏目涵盖“国内抗战动态”“南洋侨胞事迹”“救亡理论探讨”等,发行量突破万份,成为联系南洋闽侨与祖国的重要纽带。1941年12月,太平洋战争爆发,新加坡陷入危急,杨骚加入“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”,组织侨胞疏散、救护伤员,直到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前夕,才被迫撤往苏门答腊。
抗战胜利后,杨骚第一时间返回新加坡,接受陈嘉庚委托,协助编写《大战与南侨》一书。这部书以翔实的史料、饱含情感的文字,揭露了日军南侵的滔天罪行,歌颂了华侨的爱国精神,成为研究南洋抗战史的重要典籍。
父子情牵
跨时追寻续诗魂
从闽南少年到左翼文星,从抗战诗人到南洋赤子,杨骚的人生故事并未随时间褪色。他以“骚”为名,始终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紧密缠绕,以笔为枪,书写文学战场上救亡图存的壮歌,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精神印记。而这份印记的传承,离不开其子、漳州作协原主席杨西北数十年如一日的追寻与打捞,在父子两代人的“跨时空对话”中,一个有血有肉的“抗战诗星”愈发清晰。
在杨骚的文学创作中,《福建三唱》与《乡曲》无疑是两座标志性的高峰。《福建三唱》虽以“福建”为题,却跳出地域局限,以“山海关外血满地,山海关内黄沙起”的沉痛笔触,将家乡的命运与整个民族的危亡相连,字里行间满是“唤起民众共赴国难”的激昂力量。而长篇叙事诗《乡曲》则以漳州“乌石暴动”为蓝本,深入刻画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村阶级矛盾,既写出农民反抗压迫的“狂野风暴”,也传递出“打碎这乌黑天地”的坚定信念,践行了杨骚“以文字影响群众”的创作追求。正如著名学者卓如在她的论文《杨骚和他的〈乡曲〉》中评价,这部作品是杨骚“全部创作中最值得称赞的篇章”。
杨骚的创作风格并非一成不变。据杨西北介绍,杨骚早期的文字里,不乏“苦闷、感伤、幻灭”的色彩,青春的迷惘与人生的困惑,曾让他在诗中流露出对“脂粉与肉块、酒精与醉虾”的逃避式想象。不过,在国难当头之际,他的笔锋迅速转向现实,那些曾带着忧郁的诗句,蜕变为刺向敌人的利刃。这种转变,既是一位文人的精神成长,更是一代爱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刻的责任担当。
对杨西北来说,他从未觉得作为“文学史名人”的父亲遥不可及。杨西北5岁失怙,童年记忆里,父亲是会牵着他的手上托儿所的普通长辈。杨骚在日记中曾细致记录,年幼的杨西北执意独自上学,他放心不下,又不愿打消孩子的积极性,便悄悄跟在身后“跟踪”到托儿所;1956年5月2日,杨骚的日记里还留着“北已差不多五岁,问我是不是想死”“漫应之”的琐碎片段,字里行间满是为人父的温情。这些零散的记忆,成为杨西北后来追寻父亲足迹的起点。
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,杨西北踏上了一场漫长的“寻父之旅”。他先后奔赴福州、广州、北京、上海、重庆、杭州等十余座城市,走访父亲当年的左联战友、文协会友,收集散落的书信与手稿,从泛黄的回忆文章中爬梳出鲜为人知的细节。今年3月,杨西北又踏访了新加坡所有杨骚生活、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。那些关于杨骚在左联时期“讲笑话逗乐同伴”、战地采访时“忍着胃病坚持记录”、在新加坡编《民潮》到深夜的片段,一点点填补了历史的空白。历经数十年努力,他终于撰写出杨骚传记《心曲・乡曲》,将隔断近半个世纪的父子之爱重新衔接,让世人看到的不再是抽象的“文学符号”,而是有喜怒哀乐、有家国情怀的真实杨骚。杨西北在创作谈中写道,这本书,“字字蘸着心血”。
如今,在杨西北家中,摆放着一尊杨骚留日时期的头像,这尊与杨骚文学馆同款的塑像,眉眼间透着青年学子的锐气与理想,在杨西北眼中,这是父亲最本真的模样。若被问及“父亲若在世,会对当代青年说些什么”,杨西北总会坚定地回答:“两个字,‘爱国’,一定是爱国。”在他看来,这简单的两个字,既是杨骚一生创作的精神内核,也是他们父子两代人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,更是流淌在中国人血脉里、代代相传的精神火炬。
⊙漳州融媒记者 肖颖婧 文/供图
责任编辑/洪乐敏